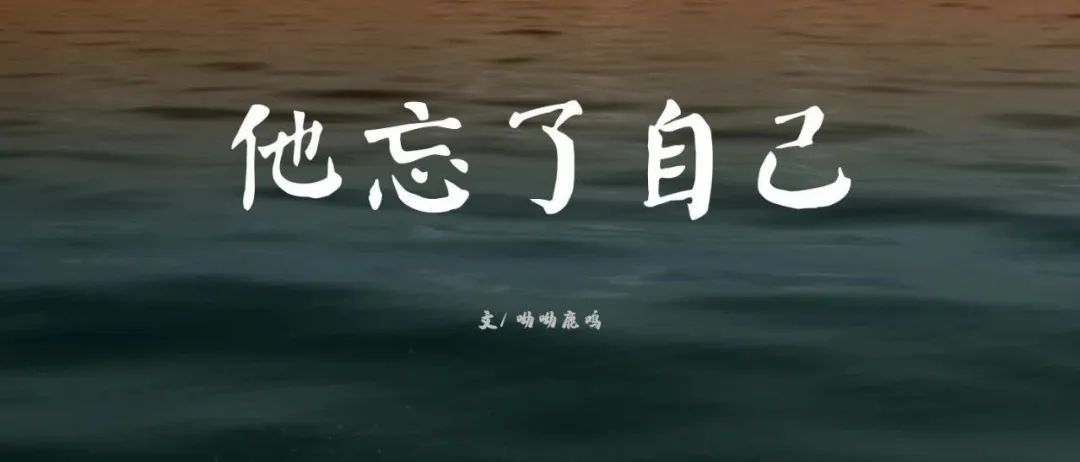去年此时,我曾经写过一篇《杜甫:无处不在的善意》。今日,念及呦呦鹿鸣读者后台留言诸君,忽有所感,遂将该文重写一遍:
我们常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那么,真正的知己,是怎样的呢?
让我们从杜甫的一首诗开始读起:
这首诗,第一个特别之处在于,杜甫明明是白天游览了奉先寺,写的却是夜景夜思。
杜甫是一位极度勤奋的诗人,留下的诗也只有1400多首,算上遗失的估计也多不到哪里去。
为什么呢?因为杜甫下笔,一定是有所感,有所通透,有所发现之后。所以,这首游览诗,他白天没有写,晚上也没有写,等到留宿一晚之后,听到了早晨的钟声,有所感,有所思,才下笔。
在杜甫眼中,奉先寺不只是一处建筑,不只是一个旅游景点,也不只是一个宗教场所,而是一个有灵魂的、暂时相遇的朋友。
让我们从杜甫这里岔开,先读一首陶渊明的《移居》:
这首诗,谈的是人与人相处——真正的好朋友,可以“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但是,这种宾主相欢共证大道的场景,有一个前提,就是第二句“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你要和对方相处几个早晨待上几个晚上,一起住宿,而不是在论坛、餐桌上泛泛一面,才能深入地、立体地理解一个人。
杜甫到了龙门寺,就是住在了那里。于是,别人写白天,他写深夜和早晨,这才会有“令人发深省”的末尾句,自然而然,毫无矫揉造作。龙门寺在洛阳龙门石窟那里,即便在唐代也属于常见景点,之所以杜甫能在寻常处“发人所未发”,留下传承千年的诗篇,正是因为他先把这座寺庙当做朋友相处了。
在杜甫留下的一千多首诗中,这首诗有些特别——透着一股佛性。
“招提”是梵语,第一句的文眼,是“境”,最后的晨钟,也是佛家关键法器,“惊醒世间名利客,唤回苦海梦迷人”。杜甫,在佛家的晨钟中“发深省”,这是一种向内、慎独的态度,与佛家“顿悟”理念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一起。由此,整首诗充满了禅意。
杜甫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在当时,还有一位大诗人,王维。王维是佛系的,文字中处处透着佛意,被人称为“诗佛”。杜甫呢,是彻头彻尾的儒家,始终关切民生、心忧天下、积极入世,即便自己的茅屋为秋风所破,他所先想到的,也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自己都没饭吃了,还在担忧别人过得好不好,真是病得不轻(事实上,他的一个儿子真的在战乱中被饿死了,而他却是赶几百里路回家才知道)。
在与奉先寺相处并写作的时候,杜甫并没有固执自己。这就是对自己所处环境、所借宿的地方最大的一种尊敬:不是给多少住宿费,而是深深地理解了对方,融入了对方。他是一个彻底的儒家,但不妨碍接纳佛家,这就是杜甫达到的格局。
杜甫这种对朋友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在写给李白的诗歌中尤为明显。
杜甫写给李白的诗,有十几首。你看,《春日忆李白》这样写的:
一开头,一种飘逸的气息就扑面而来。这种气息和李白非常接近,却与杜甫代表作品中的《兵车行》“三吏三别”等截然不同。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杜甫在怀念李白的时候,将心比心,把自己融入了李白的气场中。他忘了自己。
那么,李白是如何对他的呢?很多人说,李白不怎么搭理杜甫,杜甫写了十几首李白,李白只写了两首杜甫,甚至是嘲讽杜甫写诗很苦逼。这完全是心胸狭隘者一己之见。你看李白是怎么写杜甫的:
最后“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浓浓的杜诗味道——雄浑广阔、意境深远,与“谪仙人”李白平素浪漫飘逸气质并不相同。这是因为李白和杜甫曾经一起游历,访道寻仙,两人有共睡一条被子的友谊,才会写出这样像对方的诗句。是的,真正的朋友,就是在那个时刻,我变成你,你变成了我。杜甫与李白,两位天才待友的真诚相互激荡,洋溢在诗歌的国度。
杜甫这种善意带来的共通,在《梦李白》中是表现的极致。当时杜甫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李白了,但他担忧着李白生不逢时、被流放的命运,恨不能化身为李白:
如果把这首诗和李白自己的临终绝笔《临路歌》对照起来读:
李白临终把自己比为大鹏,飞在半空却夭折了,这不就是杜甫所写的“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吗?李白说,自己在空中中途夭折了,如今却没有为麒麟生不逢时而伤心落泪的孔子,还有谁会为我哭泣呢?这是一个仙人在世间的伤感。很可惜,千里之外的李白,无法知道杜甫这时为他写了“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这是一种心连心的理解。那个时刻,杜甫就是李白。
在临终前,贫病交加的杜甫,在洞庭湖畔写下最后一首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留下这样的句子——“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这个时候,他担忧的,还是藩镇之乱下可怜的老百姓以及这个国家难测的命运。这时,诗中流动的,不是在佛寺时的禅意,也不是与李白链接时的飘逸,只有他自己——“诗圣杜甫”。
诚敬之心,可以通神。正是因为杜甫对待朋友时总是带着那样一股发自本心的通透诚意,才会写下一篇篇于平常处见不平常、情感丰沛的诗歌,才会在往后的千百年里,让无数人的情感得到回应。
他总是忘记了自己,他成了我们。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9EDb2PbjdZ7gYjCKJGF7A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