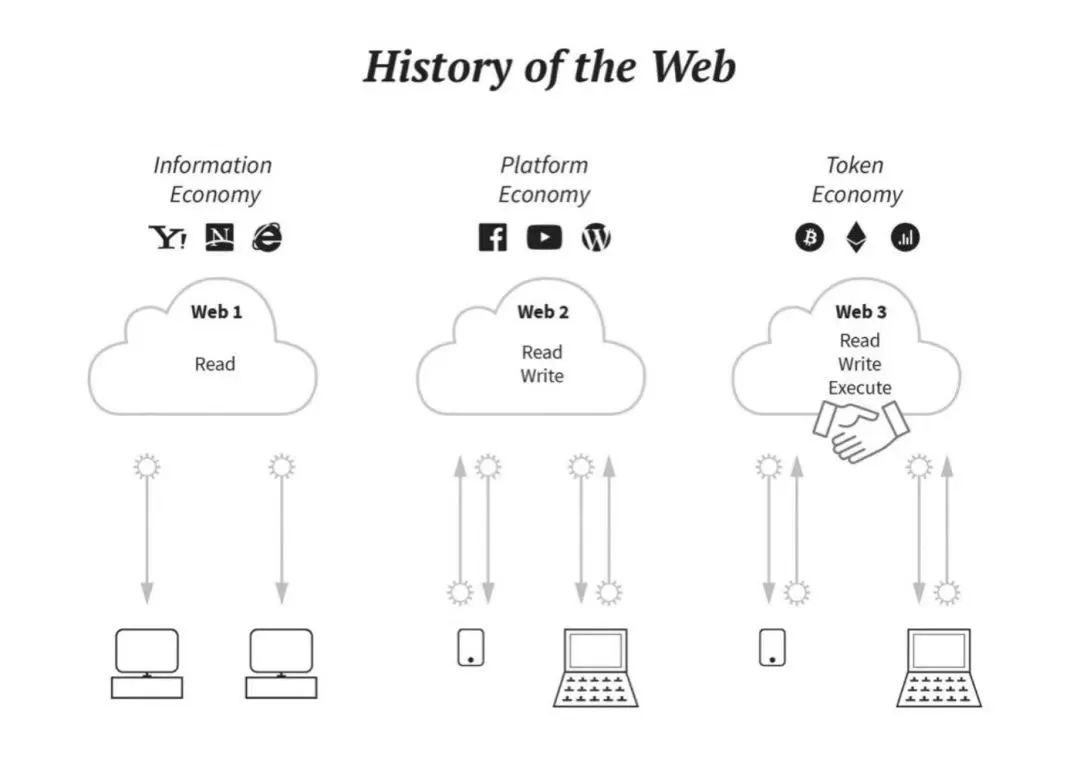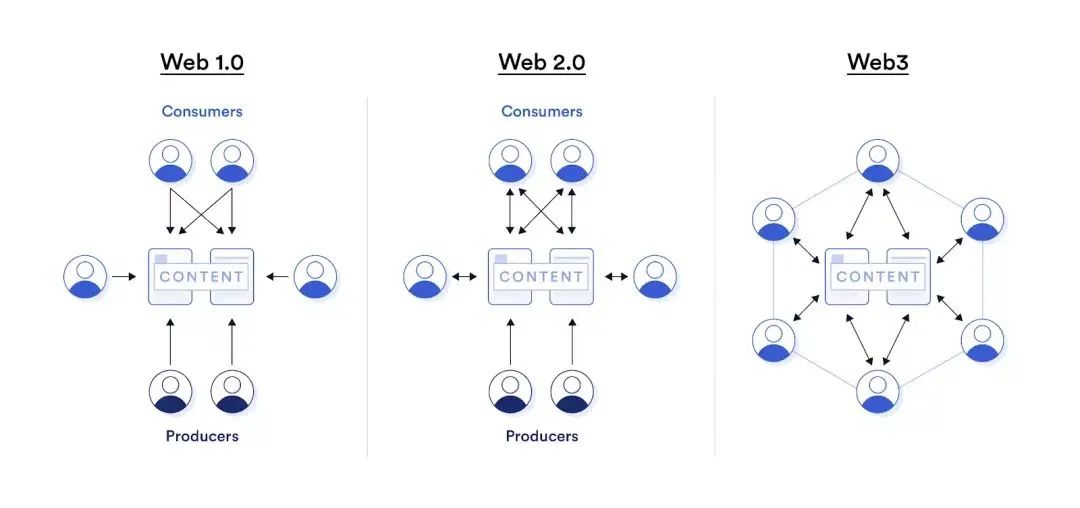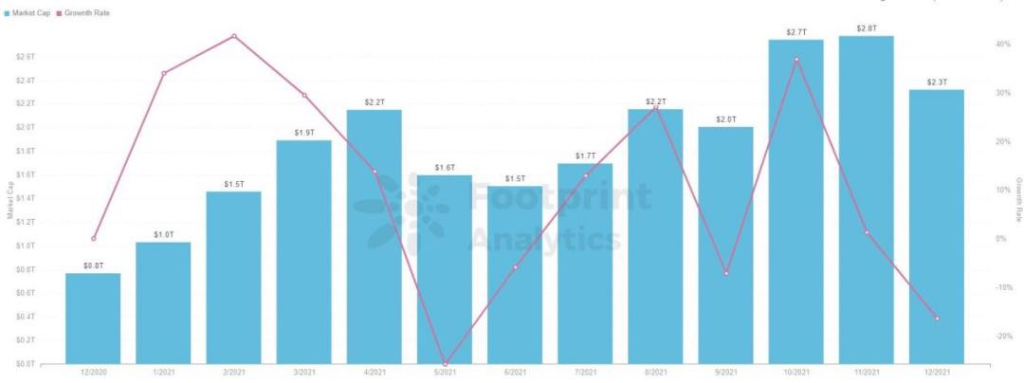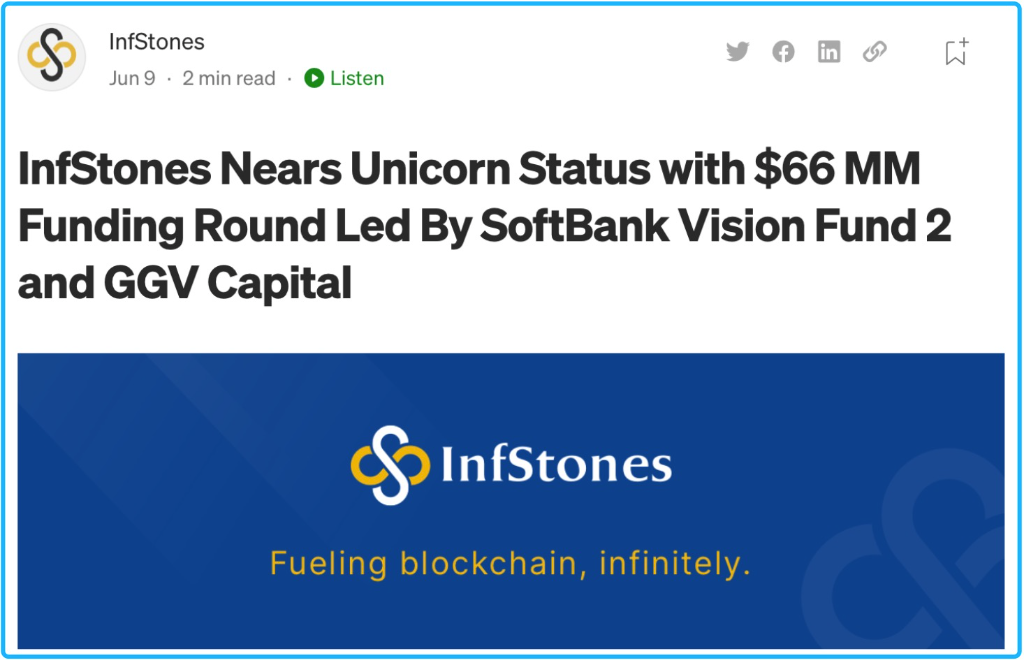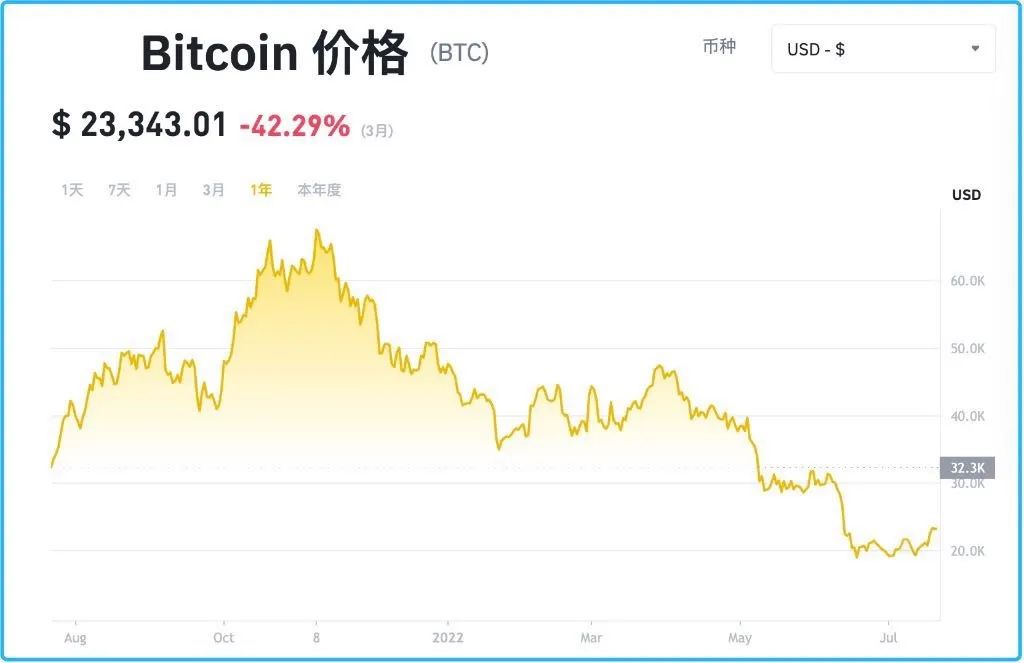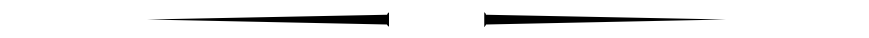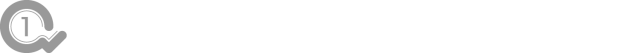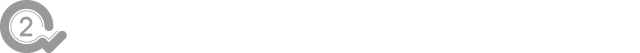· 梁云风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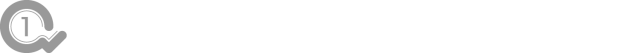 我很少在文章中讲自己的成长经历,一方面是因为自卑,另一方面也是怕将陈年往事翻出来会给身边的亲人朋友造成伤害。
我很少在文章中讲自己的成长经历,一方面是因为自卑,另一方面也是怕将陈年往事翻出来会给身边的亲人朋友造成伤害。
但是当舆论一再提“小镇做题家”这个词时,当另一个焦点人物,炫社会关系的周劼说“当年仗着自己会读书,看不起我们这种靠父母的,社会会教他做人……”,我还是打算聊一聊小镇做题家背后的真实世界。
很多人对“小镇做题家”不以为然,这个词和“凤凰男”一样,带有浓浓的俯视意味。其实在我们看来,这两个词都是带有天然褒义的,因为这都意味着我们走出了农村。
我很早就意识到了做题的重要性。我现在最早的记忆大概是3岁左右,那是家庭暴力带来的刻骨铭心的记忆。从5岁开始,破碎的家庭,亲戚的白眼,村里人的指指点点,至今仍不能忘却。我的自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在心底放大的。
改变在8岁那年产生。我出生在12月,那个时候我们家那边农村小孩都是7岁开始读书,我因为没赶在9月份出生,只能又在家放养一年。等我读一年级的时候,基本上是班上最大的那个。
我属于早熟,早熟的孩子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善于察言观色,家里大人喜欢什么,学校老师喜欢什么,我都要琢磨一下。
在家里,我每天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扫地,房间、客厅扫完,还得把外面扫一遍,这个时候,无论是外婆还是其他亲戚,都要对我笑一下。
在学校,我对老师的喜好也进行了分析,比如老师喜欢爱劳动、来学校早、听话、成绩又好的学生。我发现自己晚一年上一年级,相比身边还在流鼻涕的同学,甚至这都能成为一种优势。我主动向老师申请做劳动委员,督促同学们值日,教室里纤尘不染;我争取每天都第一个到学校,有一次因为外婆早上出去劳作,回家做饭晚了,我空着肚子赶去学校……
那个时候没有“做题”的条件,因为农村教育资源的荒芜以及家庭贫瘠根本没有多余的课外练习可以做,我就多写“小字”(“大字”是毛笔书法),一个字写四五页,所以我的字一直受到老师表扬。因为这个,还被很多同学“记恨”过。
这一切老师当然都看在了眼里,从小学到中学,我都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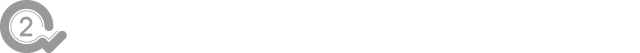 2000年的小升初是一个门槛,现在身边很多家长都在焦虑读哪个学校好,但我们那会儿,其实读初中也不是所有人的权利。我们小学毕业班56个学生,读初中的大概40人左右,有十多个学生就此辍学,大多因为成绩不好而厌学,他们很多都到沿海城市打工,或在温州的某个鞋厂,或在东莞的某个电子厂、家具厂,有的早早成家,有的单身至今。
2000年的小升初是一个门槛,现在身边很多家长都在焦虑读哪个学校好,但我们那会儿,其实读初中也不是所有人的权利。我们小学毕业班56个学生,读初中的大概40人左右,有十多个学生就此辍学,大多因为成绩不好而厌学,他们很多都到沿海城市打工,或在温州的某个鞋厂,或在东莞的某个电子厂、家具厂,有的早早成家,有的单身至今。
初中真正开始了“做题”生涯。我们那会儿读初中是在镇上,离家大概有十多公里,一般都是周日下午从家里提着米和炒好的菜到学校,在学校住一个星期,到周五下午回家。冬天还好,一般咸菜能放五天,夏天的话只能吃一两天,剩下的就得在学校食堂买菜了。我那会儿家里一般冬天给3块钱,夏天给5块钱,我们很多同学还都得从里面省下一两块钱买文具、课外资料,真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分用。
物质上的贫瘠还能克服,真正难以忍受的是精神上的荒芜。我一直对初中的老师心怀感恩,那时候是真没有多少钱能买课外资料,我们英语老师、数学老师用那种古董一般的油印机给我们印试卷,那些试卷是他们通过个人关系从外面找来的,是县里、市里甚至外省的模考卷、测试卷,很多个“体育老师不舒服”“音乐老师请假了”的时间里,我们拿着仍有油墨味的试卷,一张一张地刷完题。
最近听到张桂梅说,“人家说做题对孩子不好,我们没办法,我们只有这个办法”,我也潸然泪下。我们从小到大听家长老师说的,无非就是读书能改变命运,这也是过去几十年,中国广大寒门子弟向上的动力,所有人都信奉勤劳努力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就跟小镇做题家信奉只要读书就能改变命运一样。
今天回忆过去的求学经历,其实不是说我有多惨,我们那一代人很多人都这样,不同的是我们走出大山的方式。
去年刷屏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黄国平博士论文《致谢》,他含泪写道,“我走了很远的路,吃了很多的苦,才将这份博士学位论文送到你的面前”。而又有多少人,走了很远的路,吃了很多的苦,却依然在泥泞中负重前行的呢!
我2003年中考成绩是684分(总分750),在全校排第3,本能去县里最好的一中,但考虑到学费、生活费,我最后选择了去县里一所新成立的民办中学,因为它不仅免了我三年的高中学费,还能每个月给150块的生活费。我们那个班上30多人,都是这种情况,基本上是各个乡镇中学的孩子。
今天虽然母校早已风光不再,但对她给我的资助,我仍心怀感激。
农村的孩子读书有多难,在城市里出生的精英是很难理解的。我小学毕业班上的40多位同学,真正读高中的,连一半都不到,而考上大学本科的,更是一只手都数得过来,我那一届的小学同学最后考上211的也就我1人。
我们缺的不仅仅是眼界与学识,更多的还是机会。
今天来看,乡镇与市县里的孩子在教育资源上差距依旧很大,嘲弄“小镇做题家”,其实是在嘲弄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嘲弄社会的不公平。
并不是每一个村里人都有机会成为“小镇做题家”。最近《南方周末》刊发了一篇《“制枪村”的二十年:如何走出罪与穷》的文章,讲述贵州松桃县东北部的小山村石花村,在二十多年间,如何与贫穷斗争,走出山村,最后不得不妥协的故事。因造枪而入狱的刑满出狱人员麻三水希望孩子通过读书走出山村,不要步父辈们的老路,但2021年夏天,麻三水的小女儿考上铜仁市一所中专学校,因为一年一万多的学费生活费不得不放弃,“小女儿作出放弃学业的决定时,麻三水出狱后全家人九年的努力宣告失败”。
我有一些很聪明、学习成绩很好的同学,因为初二时交不起学费,不得不离开校园,远赴浙江打工。如今他做淘宝也小有所成,过年的时候在村里见面闲聊,他说今年要把家里老人小孩都带到温州去,“不想孩子有遗憾!”
不得不承认,“小镇做题家”在面对城里人的竞争时,有着太多的劣势。我到南昌读大学时,第一次坐自动投币的公交,第一次用电脑处理文件……军训的时候看着同学拿出各种乐器表演,又唱又跳,深深地感受到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小镇做题家”的眼里除了题目,已经承担不起更多。
这些年,我像所有的“小镇做题家”一样,如小强一般倔强地活着。不期望阶层跨越,但愿如所有从小镇上出来的人一样,为了我们的下一辈不再如生活在闭塞、没落的小镇而奋斗。
更欣慰的事是,每一个“小镇做题家”背后都有一个向阳而生的故事,这些故事的主角有打破国外氢弹垄断,让中国成为当今世界唯一一个存有30颗氢弹国家的、来自河北芦台小镇的于敏教授;有出生寒门,著作等身,通过一生的研究,终于在抗肿瘤领域做出巨大贡献的,来自于浙江永康的颜德岳院士;还有当年感动全国背着疯娘去上学的刘秀祥,他来自农村,出身极苦,大学毕业后,毅然决然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当一名人民教师。
当然,也有很多跃龙门失败,蛰伏在乡村,在城市的一角,倔强生活的,我们为了走出乡村,用尽了所有的力气。但我坚信,每一个努力走出乡村的人,他们都是奋斗者、进取者、实干者,无论成功与否,都不应该被嘲笑。我们改变不了出身,也不因出身而放弃。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mlivSGjA1mdhiyCUE9TEx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