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子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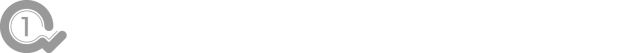 幺妹的愁与筹
幺妹的愁与筹
虽然不太相信“轻松筹”“水滴筹”这哥俩儿,这两天还是在“轻松筹”里捐了款。因为“筹”是幺妹发起的。他的父亲邱水根,肝癌晚期,时日无多,还在努力医治,这我是清楚的。
其实“轻松筹”“水滴筹”本是好东西,确实能帮到像幺妹这样贫穷又突遇变故的乡下家庭。幺妹多年前就离异,带着儿子在附近打点工,两年前,一辈子务农、身体还算健康的父亲突然被查出肝癌晚期,一场危机便陡然降临。
本地农保,县内住院能报70%,省里能报40%,出了省就是0%。病急乱投医,为了活命,总希望去更大的城市、更好的医院试试,不多久便累积出大量债务。这时“轻松筹”闪亮登场,对幺妹一家来说,无疑是根救命稻草。
东西本是个好东西,只不过因为背负太多“业绩压力”,只好采取粗暴、激烈的营销手段,比如找一群人去医院扫楼,逮谁问谁,“要不要帮你卖个惨”?甚至两“筹”为了“抢生意”,不惜大打出手……曾几何时,朋友圈仿佛变成烂大街的选秀舞台,遇上点事的人都要站上台,泪眼婆娑,“其实我也有个悲伤的故事”。
再好的产品经理,都敌不过老板、资本赚快钱的冲动,类似两“筹”的“创业——融资——对赌——不得人心乃至倒闭”的案例,每天都在大量发生。
没有了人文精神的支撑,资本越走越快,也越来越容易着急上火、脱离大部队。“不忘初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代和民众的强烈呼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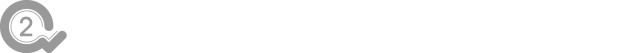 城乡版幸与不幸
城乡版幸与不幸
今天,如果要盘点“最幸福的人”,城市退休老年人无疑名列前茅。
我做背包客的时候,天南海北各大热门景区,人数最多的便是他们。他们装备齐全,不少人身背长枪、短炮各一只,连镜头都不需要切换抓起来就拍,档次更是甩我两条大街。不出去旅游的日子,则往往占据着大小城市公园、商业广场、小区空地,乃至年轻人的篮球场,听着那些欢快的音乐,看着那些轻快的舞步,就差令人惊叹“这是最好的时代”了。
从针对国人养老准备的调查报告来看,无论退休还是在职,人们对自己的养老状况普遍持乐观态度。在收集到的关键词中,“悠闲”“自由”和“享乐”几乎是大家对老年生活的共同愿景。
真是这样吗?
连调研机构的眼中都只有城市。如果将视野转向乡下的同龄人,“最好的时代”?无疑是个疑问句。
我乡下父亲一辈的叔伯们,差不多在60岁左右,这些年,每年都能查出一两个癌症晚期。乡下没有体检,县城没有体检机构,县乡医院也没有体检服务,农民每天劳作往往自觉身体健康,一旦感觉身体不行了,一查,多半有事儿,此时再去补救,往往为时已晚。
乡下的叔伯们……照片中的他们,又老了十岁
在幺妹父亲之前,去年刚有一位叫“别佬壳”的村民脑癌去世,现在又有一位叫“桂桂婆”的女人正数着最后的个把月日子……这些名字,不过是一粒粒微不足道的尘埃,在我,却是记忆中一个个强健而盛放的生命,孤独地走向干瘪和衰亡。
即便躲过大病袭扰,“老去”依然是个沉重的话题。再老一辈人,大多过得并不如意甚至是可怜。
幺妹的奶奶前两年去世,去世前,由几个儿子轮流供养。每到吃饭的时间,便摸索着用一条凳子站起来,再借助这条凳子一点一点挪到儿子家。此外的时间,便一个人坐在黑漆漆的老房子里,喃喃自语,有时大声发泄不满,只是谁也听不懂她在说些什么,村民们便认定她有点精神病。
不是儿孙们不孝顺,只是他们自己生活压力也大,多数都外出打工去了。没有外出的,也多半边务农边做点小工,难以全身心照顾她。
老人家也不是穷。
现在乡下满60岁的老年人,每个月有108元的养老金,加上逢年过节后辈的孝顺,又不需(舍)要(得)花什么钱,往往有一定积蓄。从物质上来说,千百年来他们终于基本实现了的经济独立,再怎么着也不至于饿死,算得上是好时代。
然而从精神上来说,乡村的空洞投影在他们身上,便剧化成巨大的黑洞。
我八十多岁的外婆,体弱多病,同样一个人独居在老房子里,境况还不如幺妹奶奶,她要去儿子家吃顿饭,都是难事。
我的三个舅舅,一个数年前车祸早逝,两个已搬到县城——都把一生献给了县城的房子,无不生活拮据。长期分离缺乏生活基础,老人不习惯城里,“城里”的后辈也不习惯她的“土味”,儿媳又嫌她年老事多,难以和睦相处,偶尔喊老人去城里“团聚”,也就是走个形式——城乡的断裂,清晰而又具体地体现在千家万户。
叫她来上海住,又因为晕车出不了远门(一生走得最远的“远方”,也无非是200里外的儿子家)。好在女儿多,偶尔去几个女儿家住住,又一心挂念着过得不如意的两个儿子,一边操心他们过得不好,一边操心“百年之后”不给她送终……一个乡下女人鸡毛蒜皮的、又被时代远远抛下的一生,已经像她的老房子,老无所依,摇摇欲坠。
村庄空空荡荡,同辈老伙伴也渐渐离世,还活着的人,无人可倾诉,无处可交流,孤独的黑洞将伴随他们直至最后的日子。城市还有敬老院(乡下以前也有),献爱心的人还有个地方可去,乡下呢?爱心都没有立锥之地。
现实中,精神上的空洞还无暇顾及,我的外婆最担心的,是突然生个病、摔个跤都没有人发现(事实上就有几次,还是邻居发现的)。还留在老家的父亲、大姨小姨、姨父、表兄妹们便商定,大家隔三岔五或一有时间,就去看看她。
当温暖了乡野数千年的,四世同堂、父慈子孝、其乐融融的岁月逐渐远去,人们乃至家庭内部,都日益被切割成一个个个体。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时代的“淘汰”来得太快,自前而后的“财富”与经验传承不再有意义,自后而前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上的“革命”不断冲刷,“后浪”一心摆脱乡野和传统,“前浪”日渐失语和孤独——缺乏人文传统缝合,代际之间的现实剥削和精神否定,取代了以往的长幼有序和温情脉脉,日益支离破碎。
 | 乡下的老人
| 乡下的老人
如此,乡下老年群体,代表的正是时代最落后、最失落的一面,所依者何?
幸好老人们手中还有点钱,在无知、孤独和沉默中,还有生存下去的一点点底气,否则何止老无所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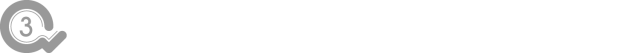 个人-集体-国家
个人-集体-国家
至今去乡下,甚至新疆、西藏、内蒙等偏远牧民家,还能见到许多人家的墙上贴着毛主席的画像。对广袤乡土而言,对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依然充满精神上的深深眷恋。
| 农家乐里的毛主席
一次与朋友老张的母亲闲聊,谈起往事,她突然顿住,脸上突然出现孩子般的笑意。她说,虽然物质上现在“才是农民最好的时代”,但还是以前幸福:
傍晚时分等待父母从地里回来,吃完饭一家人坐在门口乘凉,讲故事;
大锅饭虽然有时吃不饱,但大家没有攀比,人情简单,养老、教育、医疗什么的,也都有集体可以依靠;
乡里偶尔有放电影的人下来,方圆几里地的人就都来看。大队里也有年轻人自己组的“戏团”,虽然不专业,但都很认真;
那时的人们愿意付出,对未来认真,虽然没有什么钱(货币化程度低),虽然不能杜绝“薅社会主义羊毛”,但集体环境,依然可以相互信任、依靠、温暖……
“集体”这个词,曾在广袤乡土上闪闪发光。
梁启超在《论学会》中说,“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知识精英)疾党如仇,视会为贼。是以佥壬有党,而君子反无党;匪类有会,而正业反无会”。
千百年来,作为最正业的农,最缺的便是这“集体”。
近代以来,从孙中山的广东国民政府发动农会组织,到民国晏阳初、梁漱溟等知识分子建立的平民教育促进会和乡农学校,到建国及改革开放初期有志之士建立“农会”组织的尝试,都因为各种原因不了了之……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便成为中国农民仅有的一次集体生活体验!
“人民公社”虽然有国家推动工业化、维护工农产品剪刀差、限制农民流动等客观诉求,但上层建筑、知识精英仅有的一次真正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相结合,真正推动了广袤乡村事业的全方位建设。
1956年,国家建立农村“五保供养”和集体敬老院制度,依托集体力量实现养老,此举还为城市职工企业养老制度提供了借鉴;
1965年,毛泽东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全国大中城市有大约一半的医务人员下到农村,帮助建立起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使得农民看病、子女读书等有了集体保障;
有了集体的力量,人民公社时代的生产力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低,当时集体开垦的良田、兴建的水利基础设施,规模大、质量牢固,才奠定了“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的基础,而不少乡村水利至今还在吃当时的老本……
“集体时代”,便成为新中国乡村建设最重要的阶段,也是广袤乡土迄今为止的温暖记忆。
大集体时代,个人虽被压制,但也有了依靠,结合意识形态,最终形成了“个人(家庭)—集体—国家”的完整逻辑。改革开放后,集体不断瓦解,1985年国家正式宣布取消人民公社,乡村重归小农经济;9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对效益不高的农业领域、对乡村公共服务逐步退出,上述体系被简化成了“个人—国家”关系。扶贫这件伟大的事情上,也是国家和个人的直接关系。
于是,当一个城里人遇到问题,可以找工会、部门、社区、协会寻求沟通与帮助,而一个个张玉环、聂树斌、呼格吉勒图……遭遇不公,只能寄希望于“上天有眼”——张玉环、聂树斌们还算幸运,还有亲人几十年奔走,记者和律师一路力挺,那些没有组织、集体依靠的“罪人们”,又有多少还在黑暗中无声地等待。
直至今天,当国家要反哺三农、振兴乡村,向三农进行财政转移支付,没有了“集体”的中间力量,即使想送钱,面对数以亿计的分散农户,无法避免地存在交易成本过高、效率有待提升的困境。
这个困难迟迟无法打破,以至于许多地方的“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的推进,又难以避免地存在流于表面、进展缓慢等现象。
由此再看乡下老年人的“老无所依”(珠三角发达地区老年人“有股份”、长三角发达地区老年人被纳入城镇化户籍保障,及潮汕、客家等保留着敬老传统的地区,在此不论),不难发现,城市老年人因为有单位、企业作为“集体”积累和背书,有社区居委会、街道医院、养老院、活动中心等“集体”公共服务载体,便有了幸福的基础。
而乡下老年人,没有“集体”可依赖,同时宗族文化又被“大集体”自己扫到历史的“垃圾堆”,就算曾经可依赖的家庭和“孝道”,也已被现代商品经济冲击得面目全非。
有“集体”作为中介,“国家”就可感、可沟通、可依赖;没有“集体”、“国家”就是一个遥远的概念。《No country for old man》(电影《老无所依》)里,“暴力”后面隐藏的深深的“无力”,并不容易挣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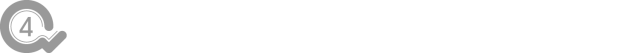 求人与求己
求人与求己
我乡下的祖辈已日暮西山,来不及讨论“老有所依”;父辈们则正在转换的档口,与有些调查报告里的乐观结论相比,呈现出的却是悲观和焦虑。
跟父亲吵了一辈子的母亲,这两年突然对父亲关切和温和起来,在上海帮我带孩子的这两年,每天必须要跟父亲视频通话。通话无非是些家长里短,多去看看老人,地里的花生、辣椒该去摘了,工作累不累之类……工作累?还是再坚持坚持,为咱再存点养老钱……
我的心中其实充满悲伤。当同龄城里人的父母在盼望着退休,计划着退休去哪里玩,计划着买这样那样的装备,我乡下的父母却在盘算着还能坚持多少年……
同样为国家做过贡献,也同样为城市、工业做过贡献,No country for country old man,当时代和“国家”都“无所依”,占人口相当比例的他们何去何从,并没有乐观的答案。
我所知的比较好的答案有二。
其一是李昌平先生的“乡村内置金融方案”。
乡下老年人多少有一些闲钱,存银行不划算又有风险(这两年不少银行存款就不翼而飞),而乡村外置金融始终不愿进入,农户贷款困难。李昌平先生便把老年人组织起来,建立金融合作社,老年人可以把闲钱投进来,支持本土乡民搞生产。
骗本乡本土的老人的钱,无疑是个天打雷劈的事儿,加上贷款需合作社里五位或以上老人联名担保,老人鉴于对自己资金负责的角度必然认真了解,便基本不会出现现代金融始终难以解决的骗贷等道德风险问题。
村民有了贷款,推动了乡村生产建设,还能支付利息。老人们的钱有了回报,更重要的,是围绕贷款、利息收益分配、公共事务建设和管理,形成集体议事体系。老人们有了自己的集体、自己的话语权,才能老有所依,乡村建设的自发性力量也才有所依……
此时,政府与其大量重复建设,大量把钱塞给贫困户,不如主导成立乡村建设基金,投入一定资本作为种子基金,吸引老年人入股,并将收益投入到地方公共事务建设。在带动在地化产融结合、盘活乡村自发建设力量的同时,解决地方养老、乡村缺乏集体及议事机构的弊病……可谓治本之策。
只可惜,这个有效的方案尚未得到地方政府部门的重视。
其二是乡村互助养老设计。
既然无所依,那就求人不如求己。
乡村可建立“互助养老社”,年满60岁可加入。60岁左右的老年人,身体往往还健康,有一定照料能力,可以参与照料社内年龄更大、身体不便的老者,并可兑换成“养老券”。当自己年龄增大或行动不便时,便可获得社内“新生”老年人的照顾,或凭券获取相应服务。
此一设计,开端需要政府的信用背书、鼓励及推动——随着中国老龄化不断加快,城市有老龄办,县乡政府也应该设此组织,并推动类似事务发展。
“个人-集体-国家”,新中国乡村发展历史表明,“个人”太弱小,“集体”无法包办一切,“国家”也绝非万能,尊重个体、依托集体(或第三部门)、国家统筹,平衡发展,而非谁进谁退,这才是美丽乡村、和谐中国的希望所在!

-
作者:刘子,民间观察派,独立思考者。上海朴人资产合伙人,乡村旅游&产业研究中心研究员。
-
参考书籍/文章:
梁启超:《梁启超论教育》
毒药君:《老无所依!日本这部良心片告诉你长寿有多可怕》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cdOk0gFzwb4m-AFGkur37Q